失去的,和寻找到的
 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——读刘登翰“侧影”的感想
洪子诚
刘登翰《一个华侨家族的侧影》(以下简称“侧影”)的这些文字,在写作过程中我就陆续读到;这次结集又重读一遍。谢冕先生说的很好,它是家史、家族史,更是心灵史。他用清丽、深情的文笔,写一个家庭、家族在大历史中的兴衰聚散,祖辈和父辈在异国的歧路荆棘、艰难谋生,写母亲在艰难竭蹶中对亲人的思念和抚养子女的含辛茹苦,更呈现了叙述者在回顾这一切时的诚挚、执着的信念和心灵轨迹。确实如谢冕所言,在这些由汗水和泪水浸染而成的文字面前,我们能“从广阔的空间领悟到他们的迷惘和渺茫,又从叙述之细微处得到感同身受的酸楚与疼痛”。大约二十年前,我曾读到登翰写母亲的诗《月亮是那条回家的路》,那些余光中式的修辞留下颇深印象。在读了他的这本回忆录之后,才真正理解“载我泅渡”“是母亲满头漂白了的岁月”,“再也无法修补”“是我猝然发作的伤口”这些句子所蕴含的伤痛。仿照当代一位诗人的说法:这是伤痛,不是伤痛的修辞学,是伤痛本身!
认识登翰已经有65个年头。1956年9月我们考入北大中文系。那些年大学生的构成与往常不同。由于国家号召在职干部报考大学,“向科学进军”,便有称为“调干生”的身份。中文系那几届,应届高中毕业生和“调干生”几乎各占一半;他们之间的年龄相差最大达到十多岁。登翰有点特别,他不是应届生,但也不是“调干”。从厦门师范毕业后在《厦门日报》工作过一段时间,却没达到满三年的标准。因此,在懵懂无知的我的眼里,他既有引领者的资格和能力,又有同属初涉世事、城府未深的亲切感。
登翰一表人才,福建当代涌现不少才华横溢而又帅呆的文学批评家,如张炯、谢冕、南帆……登翰是其中之一。他热情、感情充沛,好结交朋友,重情义,兴趣广泛,勇于探索、有蓬勃的开创精神和能力。大学期间学习成绩优秀,既写诗,写散文,也编写电影剧本,是北大学生“文艺界”的知名人士。我们入学后分配在一个班,五年里大部分时间也同住一间宿舍,无论学识和为人,都从他那里学到很多。那时选择中文系,大多有当作家、诗人的幻梦。在他的提议下,我们把自己写的诗和散文抄录在“坐标纸”上,出了两期墙报。因为是贴在宿舍里,读者肯定不会超过20人。他多次把我写的诗和小说推荐给《红楼》,它们的蹩脚无法逃避被退稿的命运。在1958年“大跃进”的狂热中,我和他跟另一个同学宣布提前进入共产主义。根据共产主义的“各尽所能,各取所需”的定义,三人将衣物和日用品都放在一起,大家任意取用。结果不到一两个星期,就发现没有干净的衫裤袜子,这才意识到我们的这个“主义”是在比赛谁更懒惰。1958年底,《诗刊》社来北大要谢冕找几个同学编写新诗发展概况,我能忝列其中也是登翰的推荐:孙绍振后来坦言,他和谢冕当时根本不知道有我这个人存在。
登翰在“侧影”这本书里,有许多笔墨情深地写他生活的城市厦门。我的老家是广东揭阳,与厦门相隔不远,况且潮州话和厦门话同属闽南方言——这是我上大学才知道的。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,北京揭阳往返可以选择的路线有两条,一是京广线火车到广州,转乘长途汽车,另一条经京沪线转浙赣线,到江西鹰潭转1957年建成的鹰厦铁路到厦门,再改乘长途汽车。后面一条时间和精力都颇费周折,却是我回老家探亲的首选。原因是喜欢厦门这个城市,也因为这个城市也属于登翰(很理解80年代他为什么那么热衷评述同是厦门人的舒婷)。那时候,从揭阳开出的长途汽车,经过粤闽边境的诏安、云霄,进入漳州、厦门,油然有了说不清的奇妙感觉:似乎是从溽热进入秋凉,人的步履和语调开始变得平缓、柔和,感染之下,你的焦躁情绪也跟着松弛,有了细察、遐思的可能。这也是为什么福建盛产才子才女的原因。在厦门,我曾寄宿登翰在中山路的家,尝过他母亲做的美味春卷。从他家步行不到十分钟就是开往鼓浪屿渡轮停泊的鹭江。沿着江边走道,曾听他讲述关于生活、写作的计划,他在爱情上的甜蜜和苦楚。因为他曾当过《厦门日报》记者,借这个关系得以在1958年炮战停息之后,在何厝的边防民兵指挥所楼上眺望隔海的金门。在鼓浪屿菽庄花园的礁石和海滩边,不约而同想起曾经喜欢的诗人那“日光岩有如鼓的涛声”(郭小川《厦门风姿》)的句子。也曾在他的鼓动下,傍晚渡海在鼓浪屿教堂(记不清是三一堂,还是福音堂或复兴堂)听《茶花女》全剧录音。小说《茶花女》我们是知道的,歌剧却毫无知识,既不知道是哪一款录音,当时也从未听说过卡拉斯、蔻楚芭丝、多明戈、小克莱伯的名字。不到四十分钟,登翰已经发出轻微呼噜声,我爱面子,用全部意志力强撑着不让眼皮耷拉下来。当晚的歌剧虽说一无所获,散场后走在安静的鼓浪屿小街,夏夜凉爽惬意的海风却难忘……奇怪的是,尽管有许多的交流,我们却从未谈过各自的家庭。我见过他母亲,也从未问过她的身世职业,也不知道登翰还有兄弟。对他的家庭情况很晚才有所了解,更多的细节则是读了他这本书之后才知晓。也许我们那时年轻,无意识中多少会以自我为中心,而且总以为父母永远不老。
上世纪90年代登翰写有《寻找生命的尊严》的散文集,偶然看到他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印有这样的题记:“失去的东西是找不回来了,即使找回来,已不是原来的东西。人生是一个过程,生命便是在永远的寻找、失落,再寻找、再失落……中。”这是他的总结,也是他的感慨。“侧影”写到很多的无法再找回的“失去”,有文字难以表述的苦涩、痛楚。但细细读过,也能体会到他自己和家庭在挫折中的坚持,那些没有明言的寻找中获取的精神财富。
1979年底,登翰从生活了20年的闽西北山区来到福州,在题为《瞬间》的诗里写道:
所有丢失的春天
都在这一瞬间归来
所有花都盛开,果实熟落所有大地都海潮澎湃
生命像一盆温吞的炭火突然喷发神异的光彩
发现和把握这一具有创生意味的神秘瞬间,是登翰对时代转折的敏感,是长久受压抑的活力得到释放的惊喜,是对积聚的能量终将喷发的期待。而这一切都根源于他自觉的失去和寻找交错的生命意识。因此,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到21世纪,他成果卓著。他热情支持年轻诗人为主体的诗歌革新运动,为这个当时受到挤压的思潮提供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依据,并深化了他对当代新诗史的研究。随后,他将学术范围扩大到台湾、香港、澳门,以及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。在和我合作编写的《中国当代新诗史》中,独立完成台港澳的部分,并在1987年,出版了当时最有学术分量的《台湾现代诗选》;这个选本体现了文学史意识和艺术鉴赏力结合的独特视野。之后他分别主持、并撰写重要章节的台湾、香港、澳门和世界华文文学史的集体项目。正如有学者指出的,他是大陆台港澳文学、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拓荒者之一,在世界华文文学史概念、范畴与阐释框架的建立上,在诸多复杂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阐释上,他的影响已经从大陆扩展到台港澳和海外的汉语文化圈,并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整合研究中引发关注。
过去,我总认为登翰从事这项工作,主要是基于他填补学科空白的动力,以及在福建获取相关资料的便利。读了“侧影”这本书之后,才理解了其中更为深层的因素。这自然是他的选择,但也可以说是课题选择了他。他的生命、情感与家庭、家族历史脉络的深刻联系,让研究者与对象之间发生关联有一种“命中注定”的必然性。文学史研究之外,他也涉足闽南等的地域文化研究,也继续着散文随笔、报告文学的写作。新世纪以来,更致力于书法,将中国传统水墨画融入书法而自成一格,出版了《墨语》《墨象》等书法集,并在福州、厦门、台北、金门、马尼拉等地举办书法展。他的研究,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理论的提升;另一显要的特色是他个人生活经验的加入,因而具有了超越知识拼接、推演的生命温度。他对当代那些“青春历劫,壮岁归来”的诗人 (公刘、白桦、邵燕祥等)的评述,也可以用来说明他自己的学术品格:“历史的断裂和重续,凝定在个人的生命里,并且在他们重续自己的曾被阻断了的社会理想、美学理想和歌唱方式中表现出来。……在他们有关个人曲折的生活经历和人生体验的表现中,凝聚着历史的沧桑。”(《中国当代新诗史》人民文学出版社版)这体现了研究者个性、经历、对人生、对世界的体验与对象之间存在着“奇妙的契合”。
这几十年,世事纷扰变幻多端,许多事情的发生出乎我们的意料。在走过或繁华或坎坷的路途之后,登翰寻找到自己精神的归属。“侧影”告诉我们,相比起那些炫目的、外在的辉煌光彩来,个体生命的尊严,对亲人的深挚的怀念,对常年生活的土地的难以割舍,是更根本的根基。晚年,他最终落脚在厦门。尽管这个城市发生了许多他并非都乐见的变化,但是,母亲生活一辈子的中山路那座房子还在(虽然已经不属于自己),沙波尾还在,凤凰木和木棉的花仍在开放,鹭江边还留着亲人的足印,习习海风中也仍能辨认出他们留下的气息……那么,对那些的失去,还有什么可遗憾的呢?
原文载于《中华读书报》2023年5月3日
作者简介
洪子诚
洪子诚,广东揭阳人,1939年4月生。1961年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并留校任教,从事中国当代文学、中国新诗的教学、研究工作,1993年起任中文系教授。主要著述有《当代中国文学概观》(合著)、《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》《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》《中国当代新诗史》(合著)、《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》《作家的姿态与自我意识》《中国当代新诗史》(合著)、《中国当代文学概说》《1956:百花时代》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《问题与方法——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》《文学与历史叙述》《材料与注释》《我的阅读史》《读作品记》等著作。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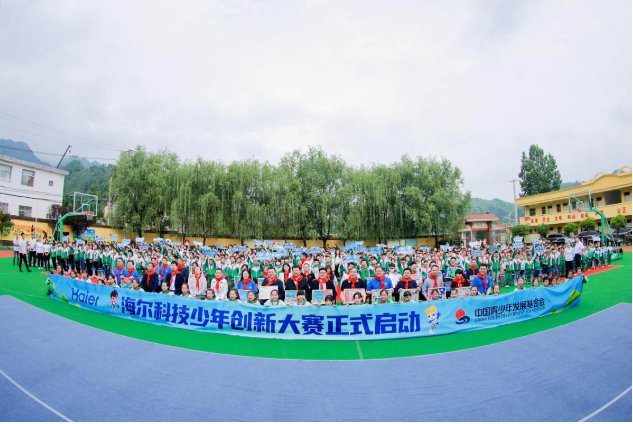
 发改委发布恢复和扩大消费二十条:餐饮消费
发改委发布恢复和扩大消费二十条:餐饮消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