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科创板日报》7月28日讯(记者 万静波 敖瑾)时值盛夏,2023年已过半,梅永红终于忙完一件筹划已久的事:把在科技部时的工作经历及此后的所思所想系统写下来,编撰成册,题为《科技十日谈》。
他在十日谈里提到了有许多工作交集的人物:原国务委员宋健、中科院院士王大珩、科技部原部长徐冠华、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、上海市委原副秘书长江上舟、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路风、华大基因创始人汪建……,这些人在政商学界都有各自的成就,而在梅永红眼里,他们都有着重要的共同气质:痴心不改的家国情怀、不畏艰难的实干精神。
 (相关资料图)
(相关资料图)
事实上,梅永红亦有相近的底色。他在8年前做出了从体制内离开的选择,这是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。因为,彼时梅永红已有在国家部委工作23年的经历,又是省部级后备干部,还具备5年地方主政经验。这时辞职,猜测和质疑随之而来。
梅永红一向在乎的是“做事”。在山东济宁担任市长时,梅永红曾说,“一个优秀企业家,应该是在做事业,是有理想的,能够表现独到的视野,比常人更多一份执着,有着强烈的责任感。”现在回过头来看,大概是在为之后的选择埋下伏笔。
这8年,梅永红一直在华大集团默默供职。他做了很多尝试,华大农业董事长,国家基因库首任主任,与碧桂园农业合作推进智慧农业,兼任北大荒集团研究院院长。近期,他还筹划发起成立深圳华谷研究院,依托这个平台开展生物经济的战略与政策研究,促进行业信息交流与对话,给政府、企业和投资者提供有价值的支持。
梅永红的办公桌上,摆着一把来自诺贝尔博物馆的折叠式木尺,上面标刻着自1800年至2000年的200年间,人类取得的所有重大科学技术成就,但其中没有一个是中国人创造的。他说,这是警醒,更是鞭策。
现在,梅永红给自己的定位依然是“科技人”。
不同寻常的选择
经过几次行程调整后,采访最终敲定在6月末的一个下午。坐在背对着门口一侧的会议长桌中间位置,摊开一本已经用了一半的记事本,梅永红平静地回顾着在商界的8年:“无论走过多少路,人生本质上都是一种经历。”
梅永红无疑比大多数人有着更丰富的经历。他出生于长江中下游一个农民家庭,不到10岁就开始在水没过大腿的稻田里插秧。直到1983年9月,梅永红考入华中农业大学农学系,他的人生开始迎来鲤鱼跳龙门的转机。
毕业那年,当时的农业部从同系九十多名学生中,选中梅永红。他顺利进入农业部农业机械化技术开发推广总站,先后担任技术员、农艺师、室主任,由此开启长达23年的国家部委工作生涯。
仕途可以称得上顺利。1995年,梅永红调任国家科委农村技术开发中心副处长,两年后转岗国家科委办公厅调研室处长。此时,年仅32岁的梅永红,在工作的第十年成为一名正处级干部。
这期间,他组织、参与了信息、航空、汽车、船舶等一系列产业领域技术创新情况的调研。如果说,早年在农业领域的学习与实践,锻造了梅永红的敬业精神,在国家科委调研室的工作,尤其是2000年前后牵头组织对大型飞机项目的调研,可以说锻造了梅永红对中国科技发展的系统思考与宏观视野。
“那段时间我们四处奔走,广泛对接。调研组内部讨论甚至争论都是家常便饭,大家对每一个问题都非常较劲,希望在争论中找到共识和答案。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,每一个人都处在忘我的状态。王大珩、师昌绪先生担任调研组顾问,虽已年届八旬,仍然不辞辛苦地多次参与座谈对话。徐冠华、郑新立公务繁忙,也经常抽出时间与调研组成员一起讨论商议。国事当头,夫复何求?”梅永红在《科技十日谈》中写到。
2003年,调研形成的《关于我国大型飞机发展战略研究报告》最终向中央提交。再经过此后一系列努力,沉寂多年的大飞机问题终于再次进入中央视野,并且被纳入国家决策程序。
2006年,梅永红升任科技部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,开始从更宏观视角,参与更高层次政策的研究和制定。此前他全程参与《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(2006—2020年)》的研究制定、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的筹备及文件起草,还参与了《科学技术进步法》的修订。
在司长任期,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落实中长期规划政策,特别是企业研发投入的税收抵扣、政府采购支持自主创新、创业投资等,每一个都是重量级、关键性政策。这些经历很不平凡,即使在国家部委也并不多见。
四年后的2010年10月,梅永红再次迎来新的事业节点——他作为中组部从54个中央部委选派到地方任职的66名中青年干部之一,到孔孟故里——山东省济宁市担任市委副书记、市长,开始主政一个800多万人口、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。
许多事或许一早就已埋下了草蛇灰线。梅永红一直倾向于做一些“正确而难”的事,只是到了地方工作后,“难”的部分似乎变得更加突出。
济宁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,一直以来煤炭都是当地的支柱产业。但长期的科技工作背景,让梅永红深知对资源的依赖不可持续。最直接的代价当时已经显现,当地因为多年采煤,出现了60多万亩的土地塌陷,而且每年还以3-4万亩的速度递增。
“我当时深感困扰的问题主要有两个:第一,为什么一切都要地上服从地下?煤炭是资源,耕地不是更稀缺的资源吗?第二,有的地方如果在地面开发,效益远超地下,为什么还要一意孤行?归根结底还在于政策打架,在于局部利益优先于全局利益,眼前利益优先于长远利益。”
问题清楚了,梅永红开始着力推动解决:“与煤炭企业管理层不断沟通,向省领导和主管部门多次反映,到国家发改委、财政部、国土部、环保部等部门反复汇报……。”
这场“跋涉”最终有了一个相对理想的结果:济宁市塌陷地问题得到多方的关注重视,全国人大领导亲自调查过问;国土部从实际出发,核减部分塌陷地的耕地指标,为大规模治理提供了政策保障;当地煤炭企业积极寻求产业转型和多元化,承担更多社会责任。
2015年,在济宁的第五个年头,在体制的第二十八年,梅永红做出了告别政府体系的决定。梅永红也理所当然地“被网红”,直到今天,还有许多人对此饶有兴趣。
看待科技发展的新视角
然后就是在华大集团的8年。梅永红坦言,离开体制的这8年并非没有纠结。“在体制内也会有,只是对这种大跨度的变化而言,可能会更突出。”
2015年加入华大,梅永红开始担任华大农业董事长,同时掌管深圳国家基因库。
国家基因库的定位非常高,它是继美国、日本和欧洲之后,全球第四个建成的国家级基因库,也是目前世界上数据量最大、功能最完备的基因库。
梅永红并非生物学专业出身,肩负的压力可以想见。他结合自己过去参与顶层设计的专长入手,“除了硬件建设,另一方面就是把基因库工作架构、工作机制确立起来,包括理事会制度、外部相关机构合作以及内部管理机制等。再有就是确立基因库未来的基本功能,共为、共有、共享”。2016年10月,基因库正式开始运行。
对于农业,梅永红则倾注了长期、特别的关注。他的微信名一直是“微山湖”,这是当时南水北调东线的一个输水渠道,为保水质安全,政府要求对湖里的网围养鱼做清理。
农民们百般不愿,但最后都服从大局,把鱼网扯了。梅永红忘不了当时的场景:有的农民一边扯,一边哭,哭祖辈“靠湖吃湖”的生计要断了。“每次想到这里,就觉得为他们做多少事都是值得的。”梅永红在采访中说。
现在,梅永红的身份是华大集团董事、深圳华谷研究院理事长,兼任北大荒集团研究院院长、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。梅永红开始把工作重心转向对科技政策的思考与梳理,以及向政府、企业以及科研院所等建言献策。
梅永红说,在政府和企业一线的工作经历,使他具备更全面的观察视角。“我的优势是,原来做过宏观研究,现在又在微观里,很容易把两者结合起来。我们过去有很多政策是原则性的。”
他对科技评价体系也深有感触。作为科技部曾经的官员,过去他也参与过不少项目、奖励和人才等方面的评审评价。进入企业后,梅永红感到,有些科技评价,实际上往往只是小循环,不能形成完整的价值闭环,无法反映在市场环境中企业的真正能力和竞争力。
“我到企业之后体会到了,任何自说自话的评价标准和体系,放到市场竞争中都是毫无意义的。因为好坏的评定最终是由市场说了算,消费者说了算。所以我特别想说的是,如果我们将技术理解为竞争力的核心,那它的评价体系应该体现的是一种价值实现,体现一个从研发到应用的完整闭环,这一点非常重要。”
在企业的工作经历,让梅永红对人才认定有了全新思考。
“华大去年在核心期刊CNNS上发表论文113篇,高居国内第一,引用数量也排在前列,而这些研究成果,都是30岁左右的年轻人做出来的。包括华大现在在做的很多具有颠覆性意义的事情,也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在领军。所以,对人才的理解,也是我到企业以后感受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不同。过去,我也会产生怀疑,但那时的感受不像今天这么具体、深入。类似这样的问题,我觉得都有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,很多过去的观点和看法都经历了修正。”
“科技人”的理想主义坚持
梅永红给自己现在的定位依然是“科技人”,“不管是在地方担任市长,还是离开政府来到了企业”。
当然,在企业还有更多更迫切的问题需要思考,“比如我们要面对竞争对手、企业的生死、技术的迭代以及消费者的苛求,类似这样的问题至少在我原来的研究范围内是不需要考虑的。”但梅永红想得更多的还是中国的科技发展道路,“包括科技战略、科技政策以及科技体制等”。
“到底应该在什么样的底层逻辑上构建我们的核心竞争力。”梅永红给出思考,是从体系的完备和协同上来着眼,“哪怕只是做一个杯子,也需要思考短板在哪里,还有没有优化的余地。我希望能更多从体系层面上来思考这样的问题,而不只是关注某个热点。对于梳理出的短板,哪怕是解决了一个,也是向前走了一步。”
在采访中,他还多次强调应当重视企业,而这种重视不仅仅是政策层面,还要包括社会文化层面,对企业和企业家的价值有新的认知。
从北京到山东,再来到深圳,他认为深圳政府对企业家的关注和重视,是深圳这些年迅速发展的关键。
“深圳政府是小政府,服务型政府。这种政府的结构和定位功能就决定了,它面对企业更多的是服务者的角色。”
如今,梅永红正致力于把这些思考重新反馈到决策体系,刚刚发起的华谷研究院,就是一个传递的出口和平台。
“虽然我还在一线,在企业中还有职位和工作,但我现在发起成立华谷研究院,推出生物经济50人论坛,就是因为我觉得有这份责任感。虽然也许微不足道,但基于我这些年的经历、思考、认知及判断,可能对政府、企业以及高校研究所有一些价值,这就是我做智库的初衷。”
如果要给梅永红的“科技人”身份加一个修饰的前缀,那么理想主义一定是不二之选。他也毫不讳言,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。
“我希望能够利用自己的知识,做更多有益于国家、有益于社会的事情,这是我这些年一直奉行的人生追求,我在北京工作如此,到山东工作如此,今天来到华大也是如此。”
附部分采访实录:
《科创板日报》:如何总结从体制内离职后的几年?
梅永红:我非常赞同一个观点:人生无论走过了多少路,本质上都是一种经历。在离职前,我已经在体制内工作28年,从农业部到科技部再到地方政府,这种经历在政府体系中也不算太多,总体算丰富。但我认为这仍是一个模式,还是固有的道路。我由衷地认为,一个人的人生不完全是恒定的,应该有更多的选择。在决定离职的当时,我没法预估跳出去以后将面对什么,但我愿意做一次尝试。
我觉得今天的社会应该给以更多包容,让更多人去尝试,你不做是没法知道结果的。当时网络上对我的选择有很多评论,但我并不在意。因为我自己知道为什么要辞职,心态是平静的。虽然也有过纠结,毕竟放弃了很多。
离职过程肯定会有很多的纠结,这种大跨度的变化超出原来的想象。但总体上讲,我觉得是一种收获,让我从另外一个维度和视角去观察社会,体验不一样的人生轨迹。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经历,我觉得自己更加丰富了,也让我在面对很多问题、挑战的时候多了一份从容。
《科创板日报》:你在个人著作《科技十日谈》中表示,体制内的工作让你形成了看问题的宏观视角,那么现在进入到企业经营一线的微观视角,你认为推动科技发展应该从哪些方面落地实施?
梅永红:我现在每天面对的问题,跟过去在政府内部面对的肯定不一样。比如我们要面对竞争对手、企业的生死、技术的不断迭代以及消费者的苛求,类似这样的问题,至少在我原来的研究范围内是不需要考虑的。但我的优势是,原来做过宏观研究,现在又在微观里,就很容易把两者结合。
我们鼓励原始性创新,这很好,但原始性创新的条件是什么,需要什么样的生态?原始性创新需要一个具有包容的环境来支持,因为它具有破坏性,是对过去技术体系、投资体系以及消费体系的一种改变甚至颠覆。
我在科技部曾一直推进政府采购政策支持自主创新,但收效不大。其实政府采购政策不是一个单纯的财务规范性制度,更多的是一项产业政策。我曾对此做了充分研究,世界各国的政府采购都属于产业政策,目标非常清楚,主要就是鼓励创新,扶持中小企业成长。
对目前而言,更值得我们关注的其实是体系的完整性。我们常说木桶效应,木桶最后能盛多少水,取决于最短板的长度,而不是长板有多高。在科技创新问题上,不能有断层,不能有短板,这就是规律。
《科创板日报》:你此前担任过市长职位,来到深圳后,如何总结深圳这座城市还有哪些在科技创新领域方面的优势?
梅:我来深圳已经将近8年,有几点我认为是值得总结的。第一是它的包容,这可能是年轻城市共通的特点。人们彼此之间的过往纠葛很少,甚至是没有,包容性也就大多了。
第二点是深圳的创新创业意识较强。我在这里接触到一些中小企业,它们真的没有太多资源,但老板就是敢闯。
第三点是深圳经过了多年的积累,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。我原来也对接过一些企业家,很多人都认为深圳具有最完备的产业链、服务链,许多在创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,包括资本、人才,都可以及时便捷地得到解决。换到一个产业链体系相对不完善的地方,可能就完全是另一种状态了。
第四点则是绕不开的政府作为。深圳地方政府是服务型政府。这种政府的结构和定位,就决定了它面对企业更多的是扮演服务者的角色。我希望深圳能把好的风格、基因坚守下去。
《科创板日报》:有关科技发展的话题,你还希望做哪些补充或强调?
梅:第一点,倡导科学精神,其内核就是质疑和批判精神。这一点我认为在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过程当中特别重要,要牢牢地确立下来。
第二点,希望我们能够重新思考,到底应该在什么样的底层逻辑上构建我们的核心竞争力。我认为很大程度上要从体系的完备性上来思考问题。整个体系的短板在哪里,哪怕是解决了一个,也是向前走了一步。
第三点,我希望更加重视企业创新。只有让更多重要的技术资源、创新资源、人才资源向企业汇集,才能说我们具备了一个更好的创新创业生态。
第四点,集中有限资源,解决卡脖子问题和关乎国计民生、国家安全的问题。如果没有集中规划,美国二战以后那么多大型科学工程不可能做出来,包括曼哈顿计划、阿波罗登月、人类基因组计划,更别说它在科学工程领域布局的100多个国家实验室,每个国家实验室都是国家目标,美国几乎最核心的科技资源都集中在这些实验室当中,中国也在吸收成功的经验。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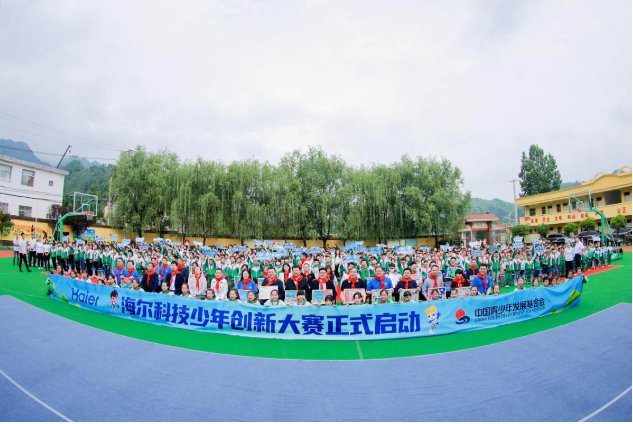
 电控发动机启动不起来,发动机电控系统故障
电控发动机启动不起来,发动机电控系统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