 (资料图片)
(资料图片)
很遗憾,因为疫情,也因为个人身体的原因,无法赴京参加谢冕先生九十华诞的诗学研讨会。在这里仅表示一位远在故乡的老同学、老朋友的祝贺。
我和谢冕相识于进入北大的第一天,迄今六十六年。人生很长又很短,没有谁能拥有两个六十六年的友谊。于我,这是很珍贵的一笔财富。我们那时年轻,在那个谢冕称为“应百花时代的召唤”共赴的“春天的约会”,尽情地挥霍青春和梦想。我们爱诗,为诗做过许多正事和傻事,也为诗尽情歌唱和为诗沉默忧伤。当年谢冕说过:爱诗如命,他以自己的毕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。他的生命是和诗联系在一起的,我们说起诗,就想起谢冕;我们说起谢冕,就想起诗。
谢冕来自福建,有着南方才子的多情和多思;但六十多年的北京生活,使他同时拥有了北方汉子的豪爽和大气。这是谢冕的人生,也是谢冕为人和作文的风格。他温柔、热情、敏锐和敏感。当欢乐来临,他是最先感受欢乐也最善于表达欢乐的人;而当山雨欲来,他又是最先预感风暴的那个人。1961年秋天,他已毕业,初婚,下放在斋堂公社。我也面临毕业,去看他,也是告别。谢冕后来回忆说:“他从北京坐了火车,又乘长途汽车,辗转了整整一天来到我工作的斋堂公社。时近深秋,树木萧瑟,枯山寒水,我们上山摘了许多酸枣,想留下一些快乐的记忆。天气是变得凉了,我们心中充满寒意,就此一别,后会难期,彼此心中怀有隐藏的不安。”我永远难忘那个离别的秋天,我们对坐在斋堂乡下的炕桌前,面对满山采来的甜中带酸还有点涩的野山枣,竟都无言。在严寒和风雪到来之前,他已敏锐地觉察到未来岁月的不安,不仅心酸和疼痛,还有各种坎坷和磨难。
在学术上,他敏锐的艺术感觉,从细微处开始,早期的《湖畔诗评》,就是这样的代表。他几乎写遍了中国当代重要诗人的个案,如他诗评集《共和囯的星光》所命名。
在熬过了那个禁言的十年,他是最早觉醒并勇敢走出来的那群人之一。他的敏感和敏锐,不再囿于局部。当1980年4月,在他参与策划的南宁诗会——新诗重生后的第一次百人盛会上,在那么多错杂喧哗的声音中,他最先敏锐地察觉出新锐的诗歌声音,最先预感到随着历史的变局所将出现的诗坛的变貌。如今重读当年那篇文章,或许不觉得怎样。但你不能不承认,文中一股鼎革的锐辩之气,迎面扑来。在当年尚还留有诸多陈旧的反对声音中,就一句宽容或包容的话,都需要莫大的勇气;何况是一个新人崛起的命题,广泛而深刻,包含了一个新的诗歌时代到来和新的诗歌生命的诞生,最终落实在一个新的美学原则崛起的哲学命题上。
谢冕的南宁发言和后来应《光明日报》约稿的那篇短文,被定格在新诗的历史上。这或许只是偶然,却又是历史的一种必然。此后谢冕直接承受着更多责难,也扛起更大的责任。他的敏感和敏锐,视野和思考,不再只在局部和个案。他着眼全局,较之前此的研究,有了一种质的变化。很遗憾,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,我的学术关注点转向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,错失了跟随谢冕学诗的机会。我不知道,在迎接新世纪和新诗百年庆诞的前前后后,谢冕自己或联合志同道合的爱诗者——包括他的朋友和学生,领衔策划、编选、撰写了多少部大型诗歌丛书?这些浩大的诗歌工程,致力于新诗的经典化,每以数百万言计,作为一代人的诗歌记忆,留在中国的新诗史上,成为历史的财富。这是谢冕最快乐的时候,也是谢冕最才华横溢、最富于创造的时候。他像北方的汉子,像一个猛士,他大块吃肉,写大块文章,做超人般的学问,尽情地释放自己,无所顾忌地创造自己,创造新诗研究的一抹辉煌!
谢冕期盼已久的百花盛开的春天,这才到来!
谢冕是个唯美者,或者是个完美主义者。他无法忍受一切丑陋、苟且和残缺。他追求美诗、美文,还有美食。或雅或俗,他不要高贵,只求完美!他生于南方,挚爱南方的优雅和精致;又长于北方,神往北方的粗犷和浩阔。他是个诗人,无论他写诗或不写诗,他都以一个诗人的定位,看待人生,看待生命。他写诗评、诗论,语言之讲究,如在写诗;他写散文,寻求的境界,至雅或至俗,亦如写诗,他是诗评界里最优秀的散文家。他的人生多彩,颠簸起伏,隐入谷底,涌上峰巅,亦如一首诗。诗不会老,诗属于青春。我怎么也不能想象,我们是在讨论九十岁的谢冕的诗学。对于谢冕,时间不是丈量生命的标尺。当我读着谢冕的《换骨记》,我觉得那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的青春的声音!
那么,让我们致敬,为一个九十岁的年轻人的青春生命!
一个新的 年代中期 在一起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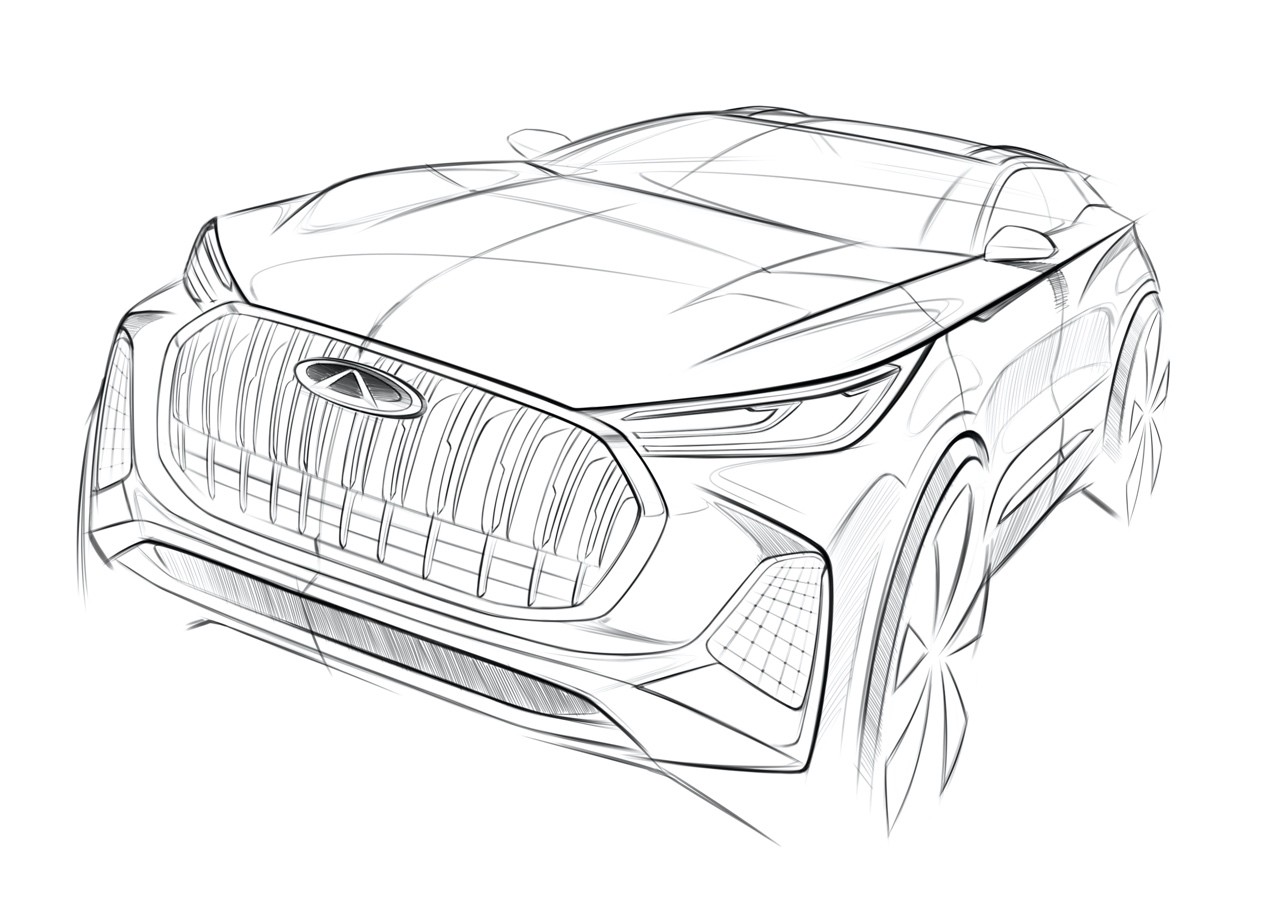


 全球百事通!内蒙古将举办2023届高校毕业生
全球百事通!内蒙古将举办2023届高校毕业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