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们那村有个奇怪的现象,老前辈中,矮男人多,但大多娶了个高女人。男人比女人基本矮一个头,最甚者矮三分之一,但架子不小,要打要骂,照样。女人虽然高大,但多为远方嫁来,举目少亲,且心肠本不硬,因而罕见“河东狮吼”。倒是一个玉树临风的男子,反其道行之,从陌生处娶了个极瘦小的女人,牝鸡司晨,反治得服服贴贴。
头号矮男,祖父辈,外来户,绰号“老狐狸”。那是1960年代前夕,开挖太浦河,动迁,老狐狸家首当其冲。搬家前夕,望着院子里水一样明晃晃的月光,尚未成人的小狐狸们怎么也弄不明白他们的脚下将要变成一条河,一条通太湖奔黄浦江的大河。他们想问,能像鱼儿一样游回来吗?但老狐狸的脸阴沉沉的。
不明白老狐狸为何要把新家安插在村子中央。按理,村头、村尾才是外来户理所当然的安家处。但老狐狸固执,而加盖几间临时稻草房对“生产队”来说也不过是寻个页面空白处盖个章而已。老狐狸抽烟,旱烟竿不离手,看看老大、老二个头不争气,空长一个“鸟”,气不打一处来。吧哒吧哒,一个劲抽烟,梦中竟把一床破棉被燃着了,一把大火,稻草房灰飞烟灭。
 【资料图】
【资料图】
老狐狸的婆娘麻脸,个格外高,脾气则温和得像刚晒过太阳的新棉袄。初来乍到,啪啪啪,接连给老狐狸生了两女一男。长大后,女的个个高挑,“末拖”小儿子更是挺拔又英俊。可惜,这一切老狐狸末能看到,火爆脾气加火烧事故,让他早早地撒手不管、魂归道山。
麻脸婆一如既往,在家默默做饭,在生产队里默默干活。满是麻坑的脸,如向日葵盘,一团和气,隐隐还流露些歉意。孩子们都叫她麻婆婆。麻婆婆的麻坑是出天花时落下的,天花是什么,很遥远,但麻婆婆有什么歉好道的呢?两个“小狐狸”继承家风,矮丈夫高女人。最后,麻婆婆的小儿子也成家了,娶得亭亭玉立、如花似玉的一个小媳妇,麻婆婆的脸更像葵花结籽,满盘灿烂。
鸟儿别枝栖。守着一个灶披间,麻婆婆一人过活。八十岁后,眼瞎了,白天就对着门坐。儿孙们把三餐摆放到她身边。大热天,难免有苍蝇嗅,听得嗡嗡声,麻婆婆也赖得赶,赶什么呢,饭苍蝇啊!倒是蚂蚁殷勤,一年四季,常绕着碗口打转。吃得“蚂蚁饭”,麻婆婆更长寿了。奇怪,脸上的麻坑越来越浅而身量却没有明显短缩。活到后来,政府出台好政策,奖励高寿,刺激得三房老儿媳妇回过头来把个麻婆婆当“活宝”,轮流供养。麻婆婆活了103岁,破纪录,为吾村第一高寿。
矮男二号,孪生兄弟。老大人称马大,老二自然叫马二。马大矮而秀气,马二憨而短矬。两房媳妇,一般高大。马大媳妇好脾气,什么事都由着马大作主。结果一赶上全民下海潮,小老头马大立马做起了小本生意,撸起袖管,菜场贩鸡。鸡半死不活则快刀斩乱麻,做成卤菜,变着法子卖。不几年,小发。手一摆,把摊位交给儿子,不问不管,享清福了。马二不然,永远在咋呼,咋呼急了,也撸起袖管,干啥,要干仗。马二媳妇不吃这套,双手叉腰,回敬:去你娘的,老娘说了算!就这样,马二总像热锅上的蚂蚁,转到哪,都愤愤然,发誓下辈子再不讨高女人。好在气愤过度,吃上卤菜没几年就病故了。
有必要说说马大媳妇,这应该是吾村又一“善婆婆”。嫁出的女儿泼出的水,孩子们叫她马婆婆。马婆婆娘家当然不姓马,而仅有的一点家族信息又极尴尬——摇头。马婆婆有“摇头病”,间歇性微微震颤,仿佛脖颈里埋了根弹簧。马婆婆的大姐嫁在邻村,来做客,我们见过,也摇头,仿佛摇得更厉害。马婆婆抽烟,神情虔诚,大家知道,她不是在抽烟而是在吃药啊。不多不少,每天一支。“吃”到晚年,逆袭成享受。
马大享清福是出外打麻将,打着打着,快马加鞭,快乐升天去了。风赶着日子,紧一阵缓一阵往前走。转眼,儿子也成了小老头,而马婆婆还是老样子,午饭后一支烟,坐在老藤椅圈里打个盹。光阴斑驳,洒落屋檐下,似猫儿跳跃,又似在捉迷藏。马婆婆呈一头雪花样的白发,她的摇头症状几乎消失了。
五月的某个午后,吃罢午饭,小老儿有事要出去,临走前,照例给老娘点上一支烟。也就一支烟工夫,马婆婆仙逝了,安坐老藤椅圈中,神态安祥,宛如入睡。烟丝燃到了尽头,烟灰如往事飘落。九九归一,马婆婆活了百岁差一岁。
矮男三号,王三。尽管王三年纪不小、资历不浅,但全村老小都叫他王三。无理由,但好像也有个理由,要是不叫他王三,那就该叫他“瘸老三”或“瘫子阿三”。双腿长短,两条小腿就像被秋风打蔫了的紫茄吊在裤管中。叫“瘸老三”不厚道,叫“瘫子”不就是骂人了。
王三老婆做事勤,人缘好。不知怎么,也是全村老小都叫她“大宝”(按理,孩子们该称她大宝婆婆)。大宝人健硕,人高马大;脸盘同样大,一副旺夫相。下嫁给王三,那是父母媒妁强做的主,她不怨命,当然也旺不了夫。嫁给王三后,完成任务一般,八年生了三男一女。奇怪的是,个个高大。有人笑问王三,是不是爬高山下的种。王三把瘸腿一挺,骂道:老子是病害苦的!(现在想来该不是小儿麻痹症?)只要看一眼东厢房的王二,高大俊朗,人家可是同胞亲兄弟啊!
王三下不了地,便搓绳,挣几个副业工分。稻草金黄,王三的屁股后面屙出黄灿灿的绳索,长长的,盘曲成一条金龙。村中顽童没上学,围坐在王三身边,看王三搓绳。王三一高兴,就给孩子们讲故事。故事大多是瞎编的,夸张,吓人兮兮,如:影子追人啦,无头人揣着自己的头颅梳头啦。最不该的是王三黄色,讲荤话,他说一个道士看到一个小媳妇在河对面洗萝卜,心痒痒的,就解下盘缠在腰间的那根神鞭放过去,神鞭昂着头,像蛇一样直探到河对面……王三沉浸于自己的意淫中,大宝回来了,直接赏赐一棍子。生产队照顾大宝,让她当集体饲养员,饲养员喂罢牲口,可以照顾一下家。王三怎么就不防着这一点!孩子们没弄明神鞭的功能,上学去了。不久,王三的女儿,出嫁了,对象就是“小狐狸”之一。乍看高矮配,其实门当户对。
回头说说王二,如果读一点书的话,王二当得起“玉树临风”形容,其妻叫小宝。怎么就叫小宝呢?“宝”在哪里,看不出;“小”倒是明明白白,个小,嘴尖刻。小宝与大宝风马牛不相及。小宝的娘家远得很,人称“西横头”,说的话如鸟语,本村人听不懂。王二只要站到门外与人多说几句,哪怕就是弟媳大宝,小宝就狠狠地把一盆水泼到门外。莫名其妙。王二索性不说话了,不说不说,养成习惯,沉默是金,人送绰号“王二哑”。
草窝里飞出金风凰,王二哑的两个女儿长得水灵灵,真叫出色。可惜只读个小学,飞不远。《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》的意境,村人终究不领悟,抱憾。
(凌子)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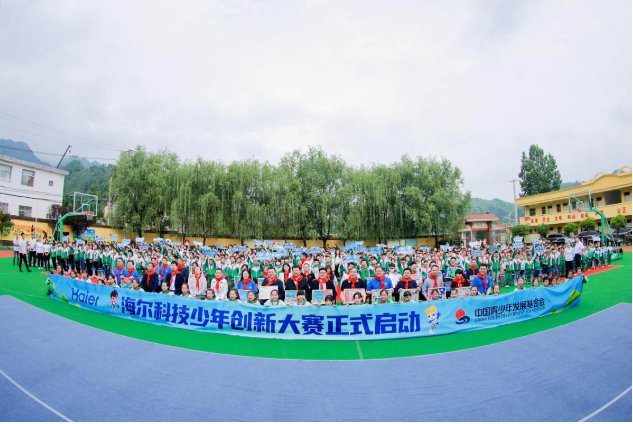
 最终幻想16剑的决心任务怎么做
最终幻想16剑的决心任务怎么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