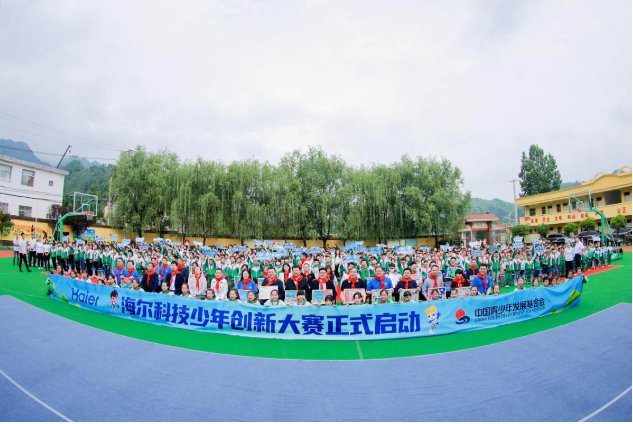陈明昊:希望年轻创作者能更有“攻击性”(主题)
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
 【资料图】
【资料图】
在戏剧领域,陈明昊可谓不折不扣的“老炮儿”。
2000年凭《第十七棵黑杨》入行,后与孟京辉合作了《关于爱情归宿的最新观念》《琥珀》《两只狗的生活意见》等多部作品,2019年,又代表中国当代戏剧首次进入阿维尼翁戏剧节核心板块IN单元演出话剧《茶馆》……
2021年,首届阿那亚戏剧节举办,陈明昊在演员与导演之外,又多了一重身份——戏剧节艺术总监。在2023阿那亚戏剧节举办期间,每天只有三四个小时可以用来睡觉的陈明昊,不仅是开幕大戏《红色》与闭幕大戏《海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》(以下简称《海罗朱》)的导演兼演员,还充当了开幕式主持人,参与了“环境戏剧朗读”,并通过先后两场采访,与羊城晚报等全国媒体恳谈。
在他看来,戏剧节提供了一个空间,让所有的参与者“按照一个倒计时的方式进行交流,这里边有很多张力和变化”,他认为这种纯粹的状态非常珍贵,“这跟现实生活不一样,现实生活里太多干扰,节奏也太快”。
“罗斯科的艺术哲思给了我很大影响”
今年在阿那亚,陈明昊带来了两部“必看”之剧。
开幕大戏《红色》脱胎于美国著名现代绘画大师马克·罗斯科在新作首展前自戕的真实故事,原剧曾获美国戏剧界最高奖“托尼奖”。2014年,陈明昊就在王晓鹰执导的中文版《红色》中饰演了故事主角罗斯科。9年后,在阿那亚,他带来了一个更具私人表达的海边版《红色》。
凌晨3点海边开演,随着5点日出而落幕的闭幕大戏《海罗朱》自首届阿那亚戏剧节亮相以来,就成为观众心中一首“沙滩上的绝美情诗”,此番再演,该剧将温暖与希望传递给了更多观众。
羊城晚报:早在2014年你就主演了王晓鹰导演版的《红色》,这次又自导自演了一个海边版《红色》。这部戏为何能给你这么强烈的创作欲望?
陈明昊:这部戏很特殊,剧中的人物罗斯科和他的表达,跟我个人的某些情感很有共鸣。比如,罗斯科的艺术精神和他的艺术哲思还挺影响我的。他人生感悟里的很多东西,我也有过类似的思考。
通过演出《红色》,我也更深地了解了现实中的马克·罗斯科,我还去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看过他的作品,有些参观者真的就面对着他的作品痛哭。
马克·罗斯科在探讨一些根源的问题,比如说宿命,比如说人的创造力总会枯竭,就像生命一样。但是他还为了一丝希望而努力挣扎——他做的事不被认可,但他还在做,最终失败了,这种悲剧英雄的内在力量挺鼓舞我的。
所以,我想通过海边版《红色》作一个大胆的自我表达。过程中,又演又导,确实让人挺分裂的,有一种“从里边往外看”的感觉。
羊城晚报:王晓鹰导演看过海边版《红色》吗?他的评价是什么?
陈明昊:他特地发了朋友圈对我表示祝贺。同时,他也说这一版《红色》是“只有演过经典版的演员,才能有这些感悟,才能有这么独特的表达”。而我也必须承认,确实是这样。
羊城晚报:时隔两年,《海罗朱》再次在阿那亚上演,并从开幕大戏变成了闭幕大戏,与《红色》占据一头一尾,这种安排有何用意?
陈明昊:《海罗朱》的核心还是莎士比亚的那句话——“那就是东方,朱丽叶就是太阳!”这句话其实给了我特别多希望,任何困难的时候,太阳照常升起。
开幕的《红色》有悲剧感、宿命感,我觉得用《海罗朱》作为闭幕大戏有抚慰人心的感觉,大家一起迎接太阳,然后各自离开,投奔各自的生活。这两个独立的作品对我来说其实是一出戏,《红色》是上半场,演出三天《海罗朱》是下半场,演出四天,中场休息三天。
“我尚未感受到爆款带来的热闹”
演戏日长,“触电”亦久。尽管是一名对戏剧舞台抱持着长久热爱与专注的戏剧人,陈明昊的“触电”经历并不少——2004年,他在个人首部电视剧《青年乌兰夫》中饰演云泽,随后陆续拍摄了《魔幻手机》《暗黑者》《沙海》《重启之极海听雷》《扬名立万》《漫长的季节》等十多部影视作品。
《沙海》《重启之极海听雷》中的“王胖子”让很多观众认识了陈明昊,而《漫长的季节》中的“马德胜”让陈明昊成为爆款演员。不过,对于陈明昊而言,热闹更多是他人与外界的,“当我演完,一切就消失了”。
羊城晚报:这几年你拍了很多的影视剧,也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喜爱。再回到戏剧的环境里,会让你有更放松、更自在的感觉吗?
陈明昊:对,戏剧像作坊一样,我们沉浸在里面生产手工作品,它没有影视剧那种铺天盖地的传播力,但我们也享受这种我们自己能够掌控的、更合乎我们生存环境的状态。
我最近确实是拍了一些影视剧,我觉得这也挺好,从表演上对我也挺有帮助的。镜头前的表演,是让我觉得特别不一样的表演,我觉得它并不容易,我得更多地去琢磨。
当我从镜头前回到舞台上表演《第七天》时,在台上表演时的好多感受发生了变化。很难简单地说这是好还是不好,但是这种能引发思考的状态也挺美妙的。
羊城晚报:爆款影视剧和爆款角色让你直面大众,或者说直面商业。《红色》和《海罗朱》又非常文艺。对你来说,会有创作状态上的分裂之感吗?
陈明昊:没有,生活状态的波动很正常,但不会影响太多。《漫长的季节》播出的时候我正在创作《红色》,很多朋友都跟我说“恭喜”“祝贺”,表扬这个剧挺好的,但我的注意力都在《红色》的创作上。其实,《漫长的季节》到现在我也还没来得及看,并没有感受到太多它带来的热闹。
羊城晚报:你没有预想到这个剧的反响会这么好?
陈明昊:没有预想。在我看来,拍电影、电视剧,演员演完后,创作的东西就跟你没关系了,“它消失了”。这跟舞台不一样,舞台是依靠演员的现场表演去进行最终解释的。我还是更习惯戏剧的表达,电影、电视剧是另外一个空间的探索。我觉得有些东西能选择,有些东西也没法选择,演电视剧也增加了我对生活的理解。
羊城晚报:很多出身舞台的演员通过影视剧火了后,总喜欢说“希望大家通过屏幕上的角色走近舞台上的我”类似的话,你也会有这种想法吗?
陈明昊:我倒没有。我觉得“看与被看”是一种关系,创作者在戏里的好多表达,观众要能把它们归拢到一个跟自己有关的思考上、问题上,才能真正地产生价值。
很多东西也不是你吆喝、呼喊过来的,就是一种能量。比如,大家为何愿意奔赴、聚集到大海边,就是因为它有能量。我觉得其实一个人不管在干什么,都是在寻找某种个人的能量状态。
“我们都受到时间规划的限制”
在阿那亚戏剧节,有一句话常被提起——“让戏剧成为一种生活方式”。陈明昊坦言,跟戏剧相处时的生活节奏,对他来说特别不一样:“我挺享受没有干扰的、只有戏剧的日子,尤其喜欢这过程中挺原始的、面对面的、专注又简单的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方式。”
在他看来,“戏剧可以不给观众答案,但得让观众有感受,甚至在某个瞬间逼迫他们思考,让他们有一种心跳的感觉。”他期待,“这种与人交流、也是与自己对话的方式能够一直存在。”
羊城晚报:当下,城市的生活节奏不断加速,给创作人做戏的时间也会随之紧张。当你跟习惯了快节奏的年轻演员合作时,需要调整的地方多吗?
陈明昊:对,现在好像你要做个什么事儿,大家都得先问你要用多少时间,才能继续聊,对吧?
我觉得我们都受到时间规划的限制,但是戏剧肯定需要更沉浸一些,戏剧需要的时间更多。对于创作者来说,有了时间的投入你才能相信很多东西。比如《红色》原版剧获了很多奖,两名演员排了8个月,剧本里提到的所有的艺术家的作品,包括哲学书,他们都去看去读,然后再来探讨生活,他们甚至去画画……所以,到了演出的时候,他们的状态很自然地就表现得像生活的某个瞬间了。因为演员经历了一个时间的磨炼,有很多东西都生长出来了。
没有这样的时间怎么办?我觉得也不能降低标准,而是努力用不一样的理念和概念,去找到一种“当下”感觉。比如我们的戏里有很多即兴的东西,也生长出来很多美妙的感觉。但“要把当下捕捉到的东西马上引领出来”,也要求演员准备得更多,想的事情更多。
羊城晚报:对于创作者来说,年轻往往意味着更新鲜的创意和创造力。对比你们自己和当下的青年创作者,你觉得戏剧承载的意义是否发生了某些变化?
陈明昊:变化肯定有,但也一定会有很多共通点。
其实,我们也在着力感受、去思考年轻一代的生活是怎样的?会去想到底有什么东西是他们享受,或者是他们在思考的。我们会好奇,对于他们来说,这个世界意味着什么?
对待我们,我希望他们能有一种“攻击性”,我希望能有一种“对抗”。这种“攻击性”就如罗斯科所说的,“孩子必须驱逐父亲。尊重他,但消灭他”。这就是时代更替的一种正常状态。
“尊重过来人”这无可辩驳,但我希望他们能更直接地把他们的能量表达出来。我觉得在创作中,艺术家们都需要这种刺激或者用这种方式去交流。
羊城晚报:最后,问一个“跳出来”些的问题——当工作强度很大时,你会做些什么让自己快速恢复状态?
陈明昊:有时会画画,我觉得当你能够专注一件事物时,状态就能调整过来,气儿也能顺过来。
现在确实有很多事儿,我得忙活。我发现我还真是没法同时干太多事儿,但只要是让我专注一件事儿,我觉得我就能行。我在郊区的山上租了一个小屋子,能远眺到北京城,屋前的小杂草丛里边还有酸枣和枸杞子,这挺好的。
现在能去这个小屋的时间真是少了,有好多事得在城市里完成。但是一有时间我还真是想在那儿待着,这是很奢侈的一件事。